毕业日3
小说 2009-08-03 08:58 阅读986 评论13 毕业日1点此进入
毕业日2点此进入
毕业日(3)
毕 业十年,我常常想起一些失去音讯的哥们儿,但从未试图去找他们。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再遇见,也许发已星星,也许四肢枯萎,但终会遇见,并且一起回忆共同享 有的往事。很多东西都会失去,有时是被夺走,有时是自己放弃。惟有往事,如果你真正珍惜,你就永远拥有。当你发现它不见了,剥开你的皮肤,掀开肉,它就在 骨头里。
此刻我想念的哥们儿,是王亚非,国贸94的北京颓废少。我们已经十一年没见面。听说他毕业后干过很多勾当,卖汽配,做客服,搞旗袍外贸。环游全国推销……一想起他打着上吊般的领带去谈业务的样子,我就忍不住笑。在我们共同享有的记忆中,他不是这个鸡//巴样。他一般穿件烂得靠谱的T恤,下身是宽松的休闲裤,上面不是有精斑,就是有油渍。走起来路来他爱扭水蛇腰,这对身高1米79的他非常不利,一下子就没有男人味了。他的脸也缺乏雄性荷尔蒙,桃花眼、薄唇、细眉毛,还好,抬头纹很重,为他挽回了一点阳刚气。他皮肤白皙,常带粉红,按相书上的话说,是“眼如秋水,色似桃花”,淫贼也。
我们开始交往在1997年,很快就成为难兄难弟。酒鬼,烟鬼,色鬼,天生就要搅在一起,就像咸要跟盐搅在一起,甜要跟糖搅在一起。对了,我还忘记介绍他真正的名字——客气的时候,我叫他贱人,不客气的时候,叫他非非。
走,干逼去。这是非非的口头禅。
要得,走,干你妈逼去。这是我的日常回复。
那时候,非非是干逼专业户,而我只是可耻的游击队员。他一年要干大小百数十次逼,艳遇多得令人发指,所以看上去相当肾虚。
他日火车逼。不是这逼动力十足像火车头,而是它来自火车。放假,非非坐火车回北京,路上老爱跟女人搭讪。有次搭讪个东北少妇,就没下车,直接补票,坐到少妇老家,干了十多天,才像倒光米的口袋一样回到北京。
他还日川工逼。说起来,那川工女生其实是他女朋友,但每次干逼后,他总要给钱。50,80,看着给。他女朋友每次也高高兴兴地收。我很奇怪,问,干嘛给钱?他说,给钱大家会开心一点。他们干了一年多,后来非非有次没给钱,就分手了。
在 大学最后阶段,非非日了个眉山逼。眉山是苏东坡的故乡,还好女孩没有长一个鞋拔子脸。他们怎么认识的我忘了,好像是非非老乡的前女友。女孩是一个宾馆的服 务员,非非每次跟她去开房间,都不出钱。日了几个月也分手了,非非苦闷地跟我说,没有共同语言,光干逼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我 很吃惊,像非非这种贱人,对女孩只有干逼的需求,怎么还会奢侈地要求共同语言呢?非非可不这么认为。有次我们喝很多酒以后,他回忆那个给钱干逼的川工女 生,声称他们有共同语言,所以他唯一爱过的就是她。我瞪他,希望把他瞪得心虚,问,真的?他奇怪地笑了起来。这是非非独有的笑容,带点讽刺,带点无奈,带 点苦,还带点孤独。我至今都记得他这种笑容,嘴巴朝一边歪过去,颧骨忽然耸起来,与此同时,眼睛变得模糊不清。
不 谈感情的时候,非非谈经济学。他喜欢用一种内置的避孕药,实惠。据说这种内置的避孕药一放进阴道就会溶解,然后杀掉一会儿要进来的所有精虫。他喜欢这玩意 儿,“放药的时候就等于前奏,抠逼,抠着抠着药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放进去了”,“没异物感,入逼即溶,还能帮助润滑”,“最重要是便宜,一包12颗,才3块6,也就是说,干一次逼3毛钱”。
说最后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神情相当小市民。
非非确实是个小市民,不但干逼要算计,吃串串香也算计。
1997年, 非非的表哥来成都开糖酒会,走之前送了两箱白酒给他。瓶子造型多样,有手榴弹,有美人鱼,最锤子的一个我怎么看都像尿壶。我们俩一个冬天就把这两箱白酒全 部喝完。基本上都是去东门外吃串串,靠兰州拉面那边的一家。每次非非都穿高帮皮鞋、脏袜子去吃。吃一大半,他就塞几十根签子在鞋帮里,拉上裤腿遮住,出去 撒尿,顺便扔签签。有时一晚要出去扔3、4次。最离谱一次,我们吃了5、6个小时,带的两瓶白酒,一瓶手榴弹,一瓶尿壶,全喝光了,最后结帐才6块钱(那时油碟不算钱),老板肯定很不热爱我们。
有次我忍不住问非非,狗直的,你不觉得签签扎脚啊?他笑了笑,说,贱人,你不知道穿两双袜子吗?
总 之,非非是贱人,小市民,但我喜欢他。他常常跟我耍小聪明,譬如有次,我没烟抽了,找他要。他掏出软天下秀,随意看看,说,只有一根了,然后掏出那最后的 一根,叼在嘴里,把香烟盒轻轻揉成团,往角落里扔掉。我走过去,捡起香烟盒,里面还躺着两大根,冲我微笑。贱人,我说,这是怎么回事?看错了看错了,他不 好意思地笑。我打算跟他绝交,他却走上来,搭住我肩膀,说,贱人,走,上东门,买啤酒,我请。
我们经常到东门一个干瘦干瘦,看上去像个奸尸犯的小伙子那里买啤酒。蓝剑啤酒,三块钱一瓶,每个瓶子还能退3毛钱。我们通常都拎个布口袋去买啤酒。等攒了一两百个瓶子,非非就找出他所有的旅行箱包,自己背一个包,拉一个箱子,我也提一个包,再挎一个,里面横七竖八地躺着啤酒瓶。然后,我们就像快乐的旅行家一样去东门退瓶子。
那 个奸尸犯其实很耿直。非非快毕业前,我们又一次在东门吃冷淡杯。奸尸犯坐在旁边一桌,带着俩不良少女。我们打了招呼。小伙子过来敬酒,说我们是优质客户。 我们仨干了好几杯。为了看那两个不良少女的乳房大不大,我们又去回敬了几杯。后来,小伙子带着俩少女先走,走的时候他一手抱一个,很得意的样子。因为太得 意,他帮我们把酒钱全结了。当天我和非非喝得不算太多,20多瓶吧,就着一盘田螺,一盘牛肉、一盘猪脑壳肉,还有土豆丝、毛豆啥的,小伙子为此付了将近100块。
小伙子走后,非非认真地看着我,说,以后你别叫他奸尸犯了,他刚才把这些年我们买啤酒的利润全吐出来了,是个有良心的哥们儿。锤子,我说,他是在那两个小骚货面前装大爷,你以为是要跟我们交朋友啊?
话虽这么说,以后我也没再叫这小伙子奸尸犯,因为我们再也没去他那里买过啤酒。非非说不好意思去。我知道,他怕人家跟我们交朋友。
交朋友是很讲究的事情,譬如说,啤酒最好跟夏天交朋友,白酒就只好跟冬天。我们买酒的人,只能跟卖春的交朋友,怎么能跟卖酒的交朋友呢?这也是大学里我坚决不入党的原因。明珠岂能暗投,我不跟黑社会交朋友。
在1998年 冬天,我们差点跟甲醛也交上朋友。当时,我们买了瓶三块钱的全兴白酒,最便宜的那种,去吃火锅。喝第一口我就觉得不对,割舌头,吞进胃里,像被人扔进了一 块烙铁。再喝几口,太阳穴突突地跳,跟着就是一炸,似乎被人抵着崩了一枪。我愁眉苦脸地喝着,又不好意思说,怕非非笑我喝不动,要我投降。
每人喝了二两,我终于受不了,说,非非,这酒不对,你有没有感觉?
对,这酒不对,肯定是他妈逼的甲醛超标,他立刻回答。
我们换了瓶酒喝。剩下的酒没要,走前倒火锅里了。如果老板回收我们锅底的潲水油,就得出他妈的大事啦。
我们还常结伴去小吃一条街最右边的东北老太那去吃饭,因为她卖的泡酒特别不错。有时,我们没钱上馆子,就去老太那打点酒,回宿舍,就着烟喝。这种喝法按照乐山话来说,叫喝寡酒。非非说这太难听了,跟喝寡妇酒似的,他说,应该叫喝干净酒。
说起干净,非非跟它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的宿舍,是我见过最可怕的宿舍,四个家伙全是埋汰人,长期在全系宿舍中卫生排名倒数第一,有次还被全校点名批评,因为卫生检查团的进去一看,就吓哭了。
没有一床被子有被套,他们盖的全是棉絮。脏衣服堆积成冢,当身上的衣服没有比冢里的更脏时,他们就到冢里去换一件。顺便说一句,除了内裤,他们的衣服都是共穿的。
一 句话,非非的宿舍是所有洁癖者的地狱。到处都是酒瓶子,就像是被抢劫过的糖酒会现场;烟头随处可见,甚至三五成群地漂在饭缸里;田螺壳、鸡翅骨头、踩得稀 烂的饭团,运气好你还可以看见一块带毛的陈年肥肉。最可怕的是那种味道,我没办法形容。那是沤馊了的汗水、精//液、脚皮屑、口痰、劣质烟酒、余音绕梁的呕吐 物的杂交,是怪味、臭味与男人味的集锦。非非宿舍的人都有皮肤病。我经常看见非非往鸡巴上搽三九皮炎平。他还要我看他龟头上的一粒疥疮,说奇痒难比。我怀 疑是性病,他说不是,性病的话,龟//头上长的是肉芽,不是温柔的小颗粒。
温柔有时也会自龟//头脱颖而出,却上心头。譬如那个晚上。
那个晚上,外面下着小雨,我们在宿舍喝酒。怕雨浇进来,我们关上了窗子。抽烟,一根接一根,说话,一句接一句。说些什么已经忘记了,反正人这辈子绝大多数说话都会被忘记的,留下的那几句也未必能让你好受。
那时候距离非非毕业只有一个多月。我说,你走了之后,陪我喝酒的贱人又少了一个。他望着我,似笑非笑,脸有桃色,像个该死的基佬。
那个晚上,外面下着小雨,我们喝得有点昏,窗子关着,透不出气。他说,开窗吧,太闷了。是啊,怎么会不闷呢?我们已经抽了一盒半烟,天下秀,软的,3块一包,在东门的胖姐那里买是2块8。非非说,胖姐真好。我说,好什么好,她那么丑,这便宜的2毛是她给咱们的精神损失费。你妈逼你损失了什么?非非说。损失了视力啊,我说,看完胖姐,再看赵飞燕,都会觉得肉头特别厚。
那个晚上,我们喝得很凶,抽烟也很凶,烟味与酒味闷在紧闭窗子的房间里,让它变成地狱的小囚间,泛着硫磺味,还有呕吐将至的气息。
非非摇晃着去打开窗子,风吹进来,给这个坟墓带来新鲜的生命力。他探出身子,大口呼吸,甚至吃起了雨丝。我走过去,推他,推不动,有点想揍他。这时候他突然说,你拉着我,我再出去一点,外面太舒服了。
外面,是六楼的外面。
他 趴在窗台上,慢慢探出身子。我紧握他的脚踝,往内使力,利用窗台将他拗住。他张开双手,像头大鸟,使劲往外伸展,直到膝盖以上的部分都在窗外的雨中。他的 拖鞋在脚板上转圈,近得就像要长到我脸上去。那拖鞋的味道好极了。我说你妈的批快把鞋子甩了。他就吧嗒两下甩了鞋子。我快拉不住他了,我的手有点发抖。 嘿,差不多了吧?我说。他却不耳食我,只管把头仰起,接吻一样地呼吸。后来,他收腹,笨拙地挪回房间,说,贱人,你也去外面走走吧。
当 我三分之二的身体都伸到夜空中时,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就像要重新做人。我仰起头,细细的雨丝扑到眼里,就像我哭了似的。凉爽的空气拳头一样打进我 的肺里,让它一窒,随即就豁然开朗。我感觉自己有十二个肺,通泰、透亮。我整个人都跟外面融在了一起。我看到了一切,或许什么也没看见。遥遥的地面向我升 过来,我向天空升过去。我有一点害怕,脑壳非常沉,又非常轻盈。非非抓住我脚的双手相当用力,但我根本就感觉不到。惟有这样,我才能觉得自己是在清凉中散 步,虚空中散步,静止中散步。
这就是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在那短短的几分钟内,我们似乎碰到了整个青春,并且感到身处其中。我们觉得希望无所不在,却又莫名绝望。
非非离校是在1998年7月上旬。他与94国贸的同学和老师都格格不入,同学嫌他傲,老师们嫌他不拍马屁。他只找了几个人在他的毕业留言册上留言,当然包括我。他没有订购专用的西南交大的毕业留言册,只随便找了本封面是日本樱花女郎的破笔记簿。
我 写了一轱辘废话,无非是说,贱人,你走了不能再见,想起来好不伤心云云。顺便回忆了我们一起喝蓝剑啤酒,一起喝甲醛,一起喝东北老太的泡酒,一起背着包去 东门外还酒瓶子等等不值一提的破事儿。他看了,沉默几分钟,认真地说,贱人,还是贱人写得最好,那些人写的都是啥逼玩意儿。
最后几个字他说得抑扬顿挫,极具感染力。这时候我才发现,他原来和我一样,是个骄傲的孤独的青年,自命不凡,虽然没有什么本领,天生看不起人,却没有证据支撑。
他离校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去火车站送他。在火车北站的站台,我们买了两瓶蓝剑啤酒。5块钱一瓶,黑,至少比那个奸尸犯黑。我一口气吹光了,他却喝得有点踉跄,中途几次洒出来。我友好地拍他的背,表示喝不完也没关系,这是最后一次。他没有停,艰难地地吹完。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看到他又露出那种孤独的骄傲的苦笑。突然他打了个嗝,似乎要吐,他赶紧用手捂住嘴,跟着就捂住了眼睛。我清晰地看见,他哭了,哭得很小,很微弱。
现在我看见非非站在我面前,骑着汽配,穿着旗袍,脸有桃色,像个基佬,要来跟我喝酒。说不定我们会酩酊大醉,说不定我们点到为止。说不定我们会抱头痛哭,说不定我们若无其事。说不定,这是一定的。

 汪 洋
汪 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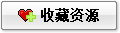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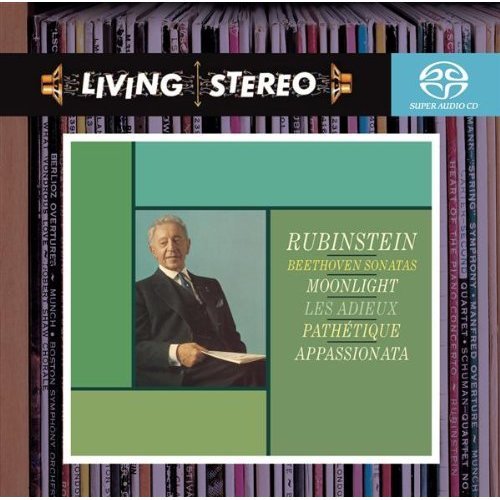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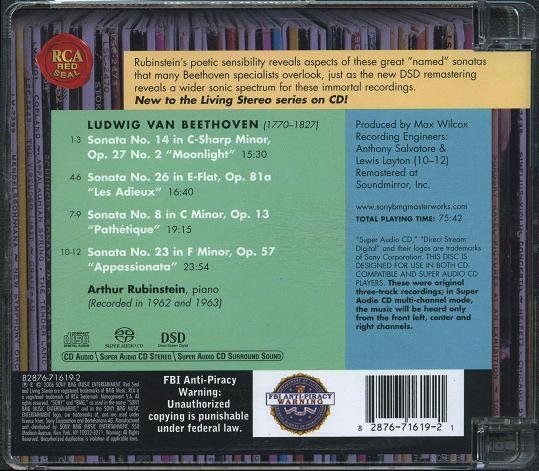
























 请!
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