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美)曼素思)扫描版[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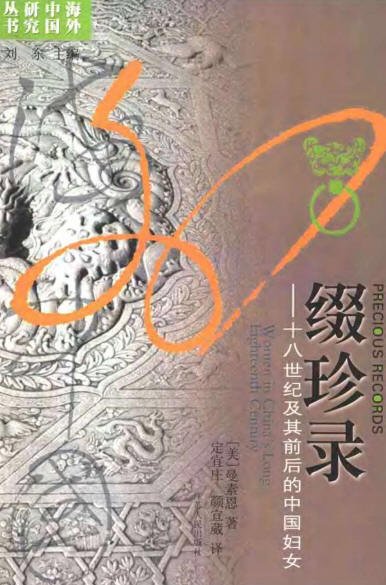
有 关中国妇女史的研究,在中国境外各地让刚刚起步,山中国女性的作品汇聚而成的宝库也还在等待着各国学者的开掘。本书仅仅粗浅地叙述了在一段短暂的历史时期 中,这些女性的感受、信仰,以及实际所做的一切。作者利用的最重要的史料均来自于女性作家的作品,主要是诗作。作者也使用了一些习见的、出自男性之手的史 料:纪传碑铭、地方史志和官方文献。这些涉及到妇女及社会性别关系的文字既出现在男性的经世致用文章——官员们为管理地方事务拟就的一些有关政策的建议 ——之中,也见于男性以礼仪、艺术和文学为对象撰成的学术文章之中。将这些习见的、由男性书写的史料与妇女自身的作品相参照,便推开了一扇通向中国女性世 界的崭新的窗口。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史料中,以传记表文为最丰富。有关中国女性的传记,已经被刊刻的就不下数千种。我们可以在地方志中、在学者刊刻的文集中所收录的碑传铭 殊、或是短篇打述... (展开全部) 有关中国妇女史的研究,在中国境外各地让刚刚起步,山中国女性的作品汇聚而成的宝库也还在等待着各国学者的开掘。本书仅仅粗浅地叙述了在一段短暂的历 史时期中,这些女性的感受、信仰,以及实际所做的一切。作者利用的最重要的史料均来自于女性作家的作品,主要是诗作。作者也使用了一些习见的、出自男性之 手的史料:纪传碑铭、地方史志和官方文献。这些涉及到妇女及社会性别关系的文字既出现在男性的经世致用文章——官员们为管理地方事务拟就的一些有关政策的 建议——之中,也见于男性以礼仪、艺术和文学为对象撰成的学术文章之中。将这些习见的、由男性书写的史料与妇女自身的作品相参照,便推开了一扇通向中国女 性世界的崭新的窗口。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史料中,以传记表文为最丰富。有关中国女性的传记,已经被刊刻的就不下数千种。我们可以在地方志中、在学者刊刻的文集中所收录的碑传铭 殊、或是短篇打述中发现它们——文集的作者总会写到他热爱和钦佩的女性。在这些作品中备受推崇的女性大多数是作者本人的或者亲朋好友的祖母、母亲、诸姨姑 婶和继母,还包括那些在西方或可以称之为圣徒的有德之人(女道土或女尼),还有一些以勇敢著称的女英雄(为父申冤、虎口救母等等)。到了帝国晚期,亦即… 以宽泛地定义为明(1368—1644年)清(1644—1911年)两朝的这个时期,所谓的列女传,事实上记述的已经全都是(因力拒强暴而死或自杀以拒 辱的)烈女或拒不再婚守节终生的寡妇的事迹。
作者简介
曼素恩获密歇根大学文学士学位、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任 戴维斯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1999―2000年任亚洲研究会主任。其第二部著作《缀珍录》曾获亚洲研究会Levenson(利文森)奖。另 与程玉溪联合主编了忡国历史上的性别书写》(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1)、目前正在撰写《张家才女外传》。
本书的副标题为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所谓Long Eighteenth Century,直译应作“漫长的十八世纪”或者“广义的十八世纪”,但这样的译法看起来既不象题目也不容易看懂,而事实上,作者在文中对她阐释的这个时 期有明确的限定,她说她沿用的概念,是何炳棣教授定义的“pax sinica(中华太平盛世)”,它发端于1683年“三藩”的被平定,而以1790年代抗清斗争的兴起以及行政腐败为结束的标志,美国学界称这一时期为 “盛清”(High Qing era)。所以我们将其译成“十八世纪及其前后”,差可近似(见中译本第二章注释1,49页)。而台湾的译本作“晚明至盛清时的中国妇女” ,我认为并不准确,因为将盛清作为一个与明朝包括晚明有着明显不同特征的重要时期,正是作者展开本书各项论述的基础。
有关“盛清”不同于 明的诸多历史特征,作者在本书第二章“社会性别”中花费了大量篇幅进行描述。她引用何炳棣教授在诸多论著中对这个时期的理解,认为清朝是在中国历史上具有 独一无二重要性的王朝,而十八世纪又是清朝统治的顶峰。虽然我国学者并不习惯以“世纪”为单位来思考社会变迁的进程,甚至提出“用世纪的方法研究清史科学 吗” 这一问题(见高翔:《近代的初曙:导论》),但西方汉学界所谓的“盛清”这一阶段,与国内学界经常提到的“康乾盛世”,在时间上确实是基本重合的。
时间上的重合以及对“盛世”的承认,并不意味着二者对这个时代的特征有着相同的理解,我国史学界对“康乾盛世”有自己的一套阐释话语,概言之有如下几 点:第一是对“国力强盛”的强调,在经济上的表现为耕地面积扩大、人口增加和国库钱粮充裕等。第二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空前巩固和发展,因为大量边疆少数民 族地区的地区是直到清前期才开始较大规模开发,并逐渐纳入全国统一的封建经济范围的。第三,康乾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任务是把处于纷争、散漫状态的中国重新统 一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大一统”。“大一统”与“康乾盛世”密不可分,存在的是互为因果也互为表里的关系。
相比之下,西方学界所用“盛 清” (High Qing era)一词则比较中性,不象“盛世”那样带有强烈的褒美色彩。他们对这个时期的描述,简言之包括其一,国家官僚机构对普通人的道德、家庭与婚姻生活的介 入达到最深的程度。其二是学术上的大规模复古,第三,人口的爆炸性增长、经济的剧烈变革,以及在社会不同阶层和地域之间人口的大量迁移与流动。还有最后, 即“盛世”的阴影也在日益清晰地呈现出来(中译本第二章,22页)。
“盛清”与“康乾盛世”,字面上看似相同,但究其实质,在阐述的立 场、角度与话语各方面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甚至可以看作是两条平行线,很难找到可比性和交锋点。而对这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阐释,理所当然会导致一系列不同 的结论。具体到《缀珍录》,作者对社会性别关系一系列变化的讨论,就都是基于美国学界对“盛清”的这套理解之上的。满族入关导致的文化裂变改变了性别关 系,使 “盛清”时期的中国建立了一套与明朝不同的价值观,社会与文化因而呈现与晚明大为不同的面貌。首先也是至关重要的,是满洲这一少数民族建立的清朝国家对家 庭婚姻等领域的干预。她认为从一开始,清朝的核心政策就注重家庭价值,提倡妇女守贞持节,抑制娼妓文化的发展。地方官吏则经常提倡妇女劳动的经济效益,也 提醒人们防范妇女参加宗教活动对“风化”的危害。第二,本书以“青楼”与“闺阁”这样两个空间来指代晚明与盛清两种不同的妇女价值观,她认为国家政策导致 “盛清”时期以“青楼”所的娼妓文化地位陡降,代之以德才兼备的名门闺秀,学术上的复古也再定义了正妻在伦理关系中的中心地位,并使歌妓边缘化。第三,作 者特别注意到了“盛清”时期江南地区因经济快速增长引发的人口和社会变化,她认为有必要从历史人口学的角度,把18世纪人们面对的日益激烈的地位竞争和旦 暮升降沉浮的人事纳入社会性别关系考虑的范围。
在从宏观上对盛清社会性别变革进行的讨论中,本书表现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学界同行研究 的尊重和汲取研究成果时具有的那种广纳百川的能力。本书的视野开阔为学界公认,我认为就源乎于此。这不仅表现在她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整体把握,汲取了美国汉 学界诸多研究成果。还尤其表现在她不断将她研究的领域,与其它妇女史研究成果的比较上。她一再提到高彦颐的《闺阁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中译本由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给予此书的启示,而本书对于“青楼”与“闺阁”、“妇德”与“才情”相对比,作为本书论述的最精彩部分,也正是建立在高彦颐 对晚明女性所作成果的基础之上的。这也使这两部书得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成为代表近年来中国妇女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我认为这种态度和做法,是我 国学者,尤其是妇女史研究者特别应该学习和借鉴之处。
事实上,有关清朝江南地区经济、社会与人口方面的研究,一直也是我国经济史学家辛勤 耕耘的领域,也有着相当深入的进展,可惜其中很多尚未被研究清史的学者充分注意并纳入到对清朝史包括“康乾盛世”的评价之中。这种状况如果能有改观,不同 背景下学者的对话,会使各项研究包括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的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
在本书第二章中,作者讨论了妇女由为人女、为人妻到为人母的角色转换过程。她比较了男女两性的不同人生轨迹,也发现了男女两性在看待人生历程的角度上存 在的差别。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她详述了盛清的学术风气对人们心目中女性的典范形象产生的影响、妇德与妇工的关系以及妇女劳动在经济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双重价 值、宗教活动对于妇女生命生活的重要性等等,为我们展示了盛清时代女性生活的精采纷呈的画卷,令我们这些习惯于以为古代女性都生活在“三从四德”的礼教束 缚下的读者感到惊奇和欣喜。她采用的很多视角和方法,在西方史学界也许并非独树一帜,但对相对沉闷的中国史学界来说,也的确令人耳目一新。我国学界对本书 的重视和赞赏多集中于此,妇女史学界对本书的借鉴,亦多着力于这些方面,对此无庸多谈。我在这里更想强调的,是本书较少为人注意的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作 者在发掘、分析和运用史料上表现出的深厚功力和勤奋精神。
我国很多学者尤其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对于国外汉学家,多年来存在一种根深 蒂固的误解,认为他们唯一为中国学者所不及之处,就是运用西方的洋理论,却因语言和文化背景等诸多限制,不擅于对中国古文献的钩沉爬梳,甚至以为他们能够 读懂几本中国古籍就已不错。我曾看到过一部中国学者撰写的选题与此书基本相同的书稿,该稿作者在并未阅读过曼素恩此书的前提下就敢断言,无论曼素恩运用了 多少理论,但在史料的掌握方面则远不及她,而她的书稿就是要“一切让史料说话”。而事实上她所征引的史料,功力深浅姑且不论,仅从数量上看就不及曼素恩的 三分之一,这便是想当然的结果。
认真发掘和分析史料,本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一个新学科的创立,尤其需要勤苦发掘新的史料资源。《缀珍录》一书 的成功就在这里。为了寻觅女性的“主体性”而尽量避免所谓的“男性的凝视(male gaze)”,作者不惜花费大量心力,希图找到女性自己的话语,她因此而广泛阅读并征引了大量妇女自己撰写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诗词。明清妇女结集刊印的诗 词为数甚钜,良莠杂陈,需要的是沙里淘金的功夫,这对于一个母语并非汉语的学者来说,以古汉语写成的诗文从字面上读懂已属不易,更何况其中隐含的种种典 故、指代和暗喻。这项工作需要作者付出何等样的艰辛,不难想见。
然而作者并未因此止步,她明白妇女诗词作为史料存在着诸多局限。从狭义上 说,以文学作品用来证史,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很容易陷入歪曲想象的误区。从广义上说,精英妇女在闺阁中抒发的个人情感,也无法代表广大妇女的真实 生活,因为“中国妇女”是一个多样化的人群,在地域、社会地位和族群等各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别。她因此而广为钩稽有关妇女问题的官私方各种文献,包括由男 性撰写的传记、文集、碑铭、方志,以及奏疏、策论,以及很难懂的经卷,并将这些文献与妇女对自己历史的书写加以认真的考辩与参照,从书末所附长达20余页 的书目(原书)就可看出作者阅读的广泛程度。
在收集史料的过程中,作者为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如此宏富的有关女性的史料、而这样大量的珍贵史 料却被长久的忽略而深为感慨。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她特别提到了,她所引用的所有史料都来自已经出版的中国文献,而非档案,其中一些是第一手资料,它们是被 精心编撰的,出版刊行的造价昂贵,而且在“盛清”时期曾为男子和女人广为传阅,她认为据此可以证明,中国妇女具有自己的一部历史,或者说,尽管我们总是需 要更多和更完备的史料,但也不能忽略对已有的丰富史料以新的方式进行解读(中译本第八章,282页)。总之,受后现代理论的影响,对主要由男性保存下来的 史料持有高度警惕心理,并要求对这些史料作彻底的审视和解构,是妇女史学打出的最具批判性的旗帜之一,妇女史对史学的贡献也正表现在这里。但我在这里想特 别强调的是,这种批判并不意味着可以在史料的运用上偷工减料,恰恰相反,对史料的广征博引和进行认真仔细的辨伪、互证,正是史家显现功力深浅之处,也是本 书作者敢于打出对男性话语的进行“颠覆”和“解构”的旗帜,并使自己的目的得以实现的前提。
三
《缀珍录》一书无疑是成功的,但作为一部开创性的作品,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有待争议的问题。举例来说,作者在提到盛清时期学术风气对妇女问题的影响 时,认为当时出现了两种理想女性的意象,一是以班昭为代表的严肃的女师,一是以谢道韫为代表的咏絮才女。这当然是从男性眼光来看,也是由男性树立起的形 象。她说前者即章学诚在《妇学》中视为正统的理想女性。而后者,被她说成是一种“幼女”形象,她们以女儿身分面对年长的男性文人,从而获取男人的怜爱。这 似乎是一种在西方学界很乐于运用的比喻方式,比较广为人知的一个例子,就是以男女来比喻中国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将位于中心和作为强势群体的汉族比喻为男 人,并声称居于边缘和弱势位置的少数民族总是以女子的意象出现。这一比喻是否合适可以姑置不论,但将才女作为一种幼女意象,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却不仅是不 太习惯,而且也嫌过于牵强。
在本书第六章中,作者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女工(红)”在妇女生活中的地位。她认为儒家的“君子”亦即男性应该 避开体力劳动,但是上层社会的妇女却应该与奴仆与佃户一起用双手从事劳动生产,一个妇女在从事女工上的能力被看作是妇女具有勤俭品质(妇德)的标志,也是 她作为良家妇女在身份上与娼妓的分野。作者甚至以每年节庆时皇后亲临祭蚕典礼来作为提倡妇德的例子。这与上述的所谓“幼女”意象一样,都多少带有刻意想象 的痕迹。须知历代皇朝固然要举行皇后亲桑的宫廷仪式,以此垂范天下妇女,但这都是配合着皇帝亲耕谡田的仪式进行的。事实上,男子之间也存在贵贱之分,从事 农工等生产性劳动为贵,经商为贱,这与女性分为良家妇女和娼妓并无本质的不同。也就是说,将对体力劳动持何种态度作为社会性别差异的一个标志,还缺乏更有 说服力的证据。
本书另一个值得商榷之处,在于她在谈论江南地区的妇女生活以及才女文化时,举出来的代表人物,是恽珠。
恽珠 为江苏阳湖人,出身属于江南世家,本人亦系才女无疑,她编撰的《国朝闺秀正始集》所收录的,大多数也的确是江南女子的作品,但她与这个人群并不因此就能等 同,这里的关键,是她个人的特殊经历:她是江南汉族士人家庭中极少数嫁给满洲旗人的女子之一,而且嫁入的还不是一般的八旗子弟,而是内务府三旗中最显赫的 完颜家族,而内务府又是清代八旗中相当特殊的一个群体。内务府包衣(满语:家的、家人之义)是皇室的家奴世仆,但作为与皇帝更亲近的“家人”,又享有外官 无法享受到的特权,既富且贵。他们是满族士大夫集团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与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的诸多区别,如果将这些区别用 一句话作一简单概括,那就是对皇权无条件的依赖和顺从。而汉族士大夫至少在表面上、在所提倡的精神和理念上还不至如此。
恽珠之所以深受清 朝道光皇帝的赞赏,被他奉为妇女的典范,说到底就是基于她对皇权的“忠”。恽珠收录边疆少数民族妇女的诗文事迹,以说明盛世的“教化”已经远播到边疆,就 是她自觉站在皇家(男性)立场、为皇家(男性)代言的典型心理。我要强调的是,这种自觉、这种品行,不仅为一般江南才女诸如袁枚门下诸多女弟子所不具备, 就是在当时满族中提倡以真性情写作的男诗人身上也是看不到的。这便使恽珠作为盛清时期妇女的代表,在典型意义和广泛程度上都大大地打了折扣。
恽珠在《国朝闺秀正始集》中明言,此书先有她的儿子麟庆插手其间,后有她的儿媳、女孙相助,这样一部出自旗人家庭、主要是旗人妇女之手的作品,也是不能 与江南女子的写作划等号的。总之,以恽珠的《兰闺宝录》为例说明“盛清”妇女已经建立了历史感,我认为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
事实上, 作者对于以恽珠为例的典型性,也有所保留和警惕,她在本书书末声称:“最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完颜恽珠作为清帝国女性代言人之引人注目,有可能与她和满族的 婚姻联系有关。汉族的女作家对于这种帝国的教化工程未必会有如此浓厚的兴趣”(中译本第八章,282页)。认识到这个事实而无法深入探讨其特性,这是不难 理解也无法苛求作者的,因为对于内务府包衣三旗的旗人群体,乃至从整体上对清代内务府制度的研究,作为一个很“偏”的领域,目前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基本 上还是空白。
本书自问世迄今已经七八年,从我国学界的研究看,效仿该书的选题、理论和视角者有之,但能够超越该书的视野,寻找 到新的、为西方学界未尝注意到的研究题目的却不多见,这固然是一个新学科起步时难以避免的现象,也与目前学术空气的浮躁有关。而本书的特点,诸如在搜罗运 用史料方面的扎实勤奋、求证时的认真谨慎,以及对待同行成果的尊重,都能够给有志于此道者以启示,说到底,本书的成功并不在于那些让人看起来眼花撩乱的理 论,而恰在于那些并不起眼的史学基础,这才是我们最应该重视和学习的。
[1]该书取名Precious Records,据台湾中研院胡晓真先生解释,这一词“一方面指涉书中用以代表盛清妇女典范意识的《兰闺宝录》一书,一方面暗示现代妇女史学者珍重处理各 种妇女材料的心情,更重要的是点出妇女史研究成果对整体历史观的重要影响与启示”(胡晓真:《皇清盛世与名媛阃道——评介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是很允当的。笔者将其译为《缀珍录》,即取此说的第二种含义。几年前曼素恩教授来北京,笔者曾就此书译名与她当面商讨,亦得到她对 《缀珍录》这一译名的首肯。
[2]曼素恩此前还著有《地方商人和中国官僚,1750—1950》(1987年)一书。
本资料来自互联网,限个人测试学习之用,不得用于商业用途,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删除。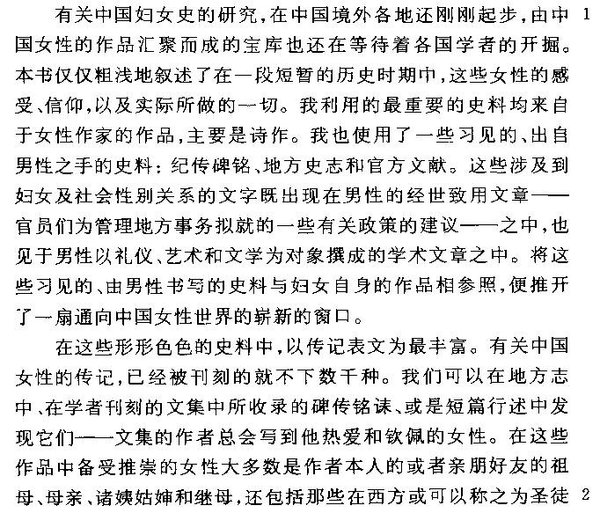
目录: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社会性别
第三章 人生历程
第四章 写作
第五章 娱乐
第六章 工作
第七章 虔信
第八章 结论:贯穿于不同地域与时期的社会性别关系
附录 清代女作家的地域分布
引用书目
译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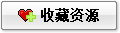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